0
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与“排除合理怀疑”的把握
2022/5/18
【裁判要旨】
现代刑事诉讼中,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已成为一项普遍性原则,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在特定情况下,被告人需承担证明责任。“排除合理怀疑”是我国“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在主观方面的解释与要求,是法官在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之后,产生的对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内心确信。
【案情】
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王某。
被告人王某,无业,因犯盗窃罪200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2011年6月2日刑满释放;因盗窃行为分别于2005年8月被处罚款100元,2005年9月被处行政警告,2005年10月被处治安拘留十四日、劳动教养一年,2007年8月被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因吸毒行为于2014年1月被责令接受社区戒毒三年。
2014年8月23日至12月23日期间,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多次入户或者进入他人公司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合计430余万元。具体如下:
1.2014年8月23日,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青湖路1070弄桂花园小区109号唐某父母家中,窃得一部价值3230元的苹果牌IPHONE5S手机、一台价值2032元的苹果牌IPAD平板电脑、一部三星手机以及现金若干。
2.2014年8月26日,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青湖路1023号晨兴商务楼206室上海易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公司)内,窃得一根男士铂金项链、香烟以及现金若干。
3.2014年12月19日,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1555弄佳邸别墅小区168号周某家中,窃得一部价值792元的苹果牌IPHONE4手机、一条价值11500元的千足金项链、一块欧米茄牌手表、一部苹果牌IPHONE5手机以及现金若干。
4.2014年12月17日至12月23日间,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1555弄佳邸别墅小区170号蒋某家中,窃得一枚钻石戒指(其中裸钻价值2749100元)、一个价值356600元的镶嵌钻石挂坠、一对价值49400元的TIFFANY牌钻石耳环、一条价值14800元的宝格丽牌红绿宝石加珍珠钻石项链、一条价值32000元的宝格丽牌18K项链、一个价值650000元的翡翠玉壶摆件、一个价值450000元的翡翠黄瓜形雕刻玉摆件、一条Pt750项链、一块TIFFANY牌白金钻石手表、一个和田玉龙鱼形雕刻摆件。
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月6日间,被告人王某独自或者指使其女友周某在贵州省遵义市将窃得的千足金项链、TIFFANY牌钻石耳环、宝格丽牌18K项链等赃物进行销赃。2015年1月8日,公安机关在贵州省遵义市将王某抓获。后公安机关在王某随身物品中,其女友周某居住的贵州省遵义市白沙路自来水家属院2栋201室内以及收购金银饰品的店主处分别查获被窃的苹果牌IPHONE5S手机、苹果牌IPAD平板电脑、苹果牌IPHONE4手机、千足金项链、裸钻、钻石挂坠、TIFFANY牌钻石耳环、宝格丽牌红绿宝石加珍珠钻石项链、宝格丽牌18K项链、翡翠玉壶摆件、翡翠黄瓜形雕刻玉摆件等财物,并将查获的上述物品发还给各名失主。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王某犯盗窃罪。被告人王某否认公诉机关指控的4节盗窃事实,辩称其未到过被害人唐某父母、周某以及蒋某家中,去过晨兴商务楼内的“香港纯K”找一个女性朋友,不记得是否经过易成公司,未实施盗窃,涉案物品系其从他人处收购的。其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王某犯有盗窃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恳请法院本着“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罚当其罪”的原则,对王某无正当理由、持有赃物的行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量刑。
【审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入户或者进入他人公司窃取他人财物,价值43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王某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王某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盗窃罪判处王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五十万元;查获的赃物予以追缴发还各名被害人(已发还),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某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被告人王某系零口供,其到案后始终否认实施过盗窃,辩称未到过现场,被查获的物品系从他人处收购得来。公诉机关一共起诉指控王某实施了四起盗窃,其中指控王某实施的第一节桂花园小区109号和第三节佳邸别墅小区168号盗窃案的主要证据有:被害人发现家中失窃后随即报案;公安人员抓获王某后,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了唐某父母失窃的苹果牌IPHONE5S手机和苹果牌IPAD平板电脑,从王某的女友周某暂住处查获了周某失窃的IPHONE4手机;王某将周某失窃的千足金项链出售给“恒生饰品”店的潘某,后公安机关从潘建处调取了该条千足金项链。公诉机关指控王某实施的第二节易成公司盗窃案的主要证据有:易成公司员工发现公司内发生盗窃案随即报案;从王某血样中提取的DNA,在D8S1179、D21S11等基因座上,与易成公司内所留果皮中具有相同的基因型,似然比率(LR)为2.27×1016,不能排除为王某所留;公诉机关指控王某实施的第四节佳邸别墅小区170号盗窃案的主要证据有:被害人发现家中失窃后随即报案,从被告人王某血样中提取的DNA,在D8S1179、D21S11等基因座上,与被害人蒋某家中卧室梳妆台抽屉上、玻璃上、大、小木盒上可疑斑迹处粘取物具有相同的基因型,似然比率(LR)为2.27×1016,不能排除为王某所留;从周某群暂住处查获了蒋某失窃的部分物品。
由于本案中没有关于王某实施盗窃的直接证据,而王某又对此提出辩解,根据现有证据能否认定王某实施盗窃,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在审判过程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对于起诉指控的第一节桂花园小区109号和第三节佳邸别墅小区168号失窃案,虽然王某及其女友周某持有部分失窃物品,但是没有证据证实王某曾到过犯罪现场,并通过实施盗窃行为获取失窃物品,故此两节不能认定王某构成盗窃罪,只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王某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起诉指控的第二节易成公司失窃案,虽然根据现场遗留物品的DNA鉴定结果,王某确曾到达过犯罪现场,但失窃物品均未在王某及其女友处起获,不能排除王某是正常进入该场所,仅凭王某到过现场,不足以认定其实施了盗窃行为。对于起诉指控的第四节佳邸别墅小区170号失窃案,虽然根据现场遗留物品的DNA鉴定结果,王某曾到达过犯罪现场,部分失窃物品在周某处起获,但是不能完全排除系他人盗窃,王某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赃物,以及王某以盗窃为目的到达现场,但因其他窃贼捷足先登而构成未遂的情形,故此节亦不能认定王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只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辩称从其随时携带的物品中和其女友周某暂住处查获的物品系从他人处收购得来,其应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但是王某无法提供出售者的具体情况;进入易成公司需要密码或者门禁卡,外人不能随意出入;晨兴商务楼内虽然有“香港纯K”,但是没法从“香港纯K”直接进入易成公司。王某亦称其到过晨兴商务楼,去“香港纯K”找一女性朋友,但是无法提供该女性朋友的具体情况。结合王某无业,并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应当认定其实施了盗窃。
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解决本案争议焦点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被告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以及如何理解与适用“排除合理怀疑”。
一、在例外情况下,被告人仍要对特定事项承担证明责任
现代刑事诉讼中,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已成为一项普遍性原则,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然而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尽管法文化和法传统有所不同,但在遵循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出于各种考虑,在立法和判例上都认为被告人在例外情况下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例如,根据英国1957年《谋杀法》的规定,控方指控被告人实施杀人行为,并举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有直接关系时,被告人如果否认谋杀,辩称意外事件所致或征得对方同意,则必须承担提出如此主张的证明责任。在美国证据法上,对于下列情形,被告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特定事项的义务:(1)如果被告方在辩护时提出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或不适于接受审判,被告方应对此提出证据加以证明;(2)如果某制定法规定,在没有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特殊情况或例外情况下,实施某种行为就是非法,那么被告方就有责任举证说明存在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特殊情况或例外情况;(3)如果被告人主张其行为曾取得许可、出于意外事件、受到胁迫、为了自卫等,此时便负有举证证明存在上述情况的责任;(4)如果被告方意图推翻制定法对某些事实的推定,或者意图援引法律条文中的但书、例外或豁免,这时被告方也负有证明责任。再如根据日本《刑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二人以上施加暴力致使他人受到伤害,在不能辨认所加害的轻重或不能辨认是何人所伤时,虽非共犯也应依共犯的规定处断。也就是说对同一人施暴的行为人,在检察官不能查明是谁造成何种伤害后果的情况下,嫌疑人负证明自己行为及其后果的责任。
借鉴国外关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立法和实践,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仅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而且在其他案件中和对某些程序性问题也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具体包括:一是被告人对某些积极抗辩事由应当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针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了新的主张,这一主张提出与否直接影响到罪与非罪或罪行轻重的认定,然而这一事实却并未被控方所掌握,被告人需对此承担证明责任。例如,控方指控甲犯有故意杀人罪,甲认可了故意杀人的事实,但提出了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这种情况下,甲对其辩护主张就需承担证明责任。因为如果甲不能举证证明其正当防卫的辩护主张具有合理的可能性,那么法官很可能要根据控方所指控的事实判甲有罪。二是存在一个可反驳的推定时,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对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构成要素以外而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从而影响到定罪量刑)的某些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方并不需要举证证明,或者仅需间接证据证明,即可推定这些要素存在时,如果被告人不对此提出证据进行辩解,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这里,被告人的辩解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义务。被告人这种提出证据进行辩解的义务是一种证明的负担,即证明责任。[1]三是对于独知的事实,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依据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实而提出某种主张的当事人必须证明他所依据的事实,否则将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四是主张精神不正常的事实,被告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对人们的行为一般都推定为是在神志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行为人是理解其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的,因而对行为人的精神状态是没有必要加以证明的。基于这一推定,控诉方在指控某人犯有某罪时,对被告人犯罪时精神状态的正常性是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的。一旦被告方提出行为时精神错乱,实际上是对这一推定的否定,因而证明责任就必然落在被告人的肩上。五是被告人主张其不在犯罪现场的,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犯罪时被告人是否在现场,是涉及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的重要事实之一。被告人声称自己在案件发生的时候不在犯罪现场,被告人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只要举出证据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就可以了,至于证据是否充分,并不影响其证明责任的完成。六是被告人主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七是对某些程序性问题,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广义上的证明对象说,程序法上的事实也可以作为证明对象。因此,关于回避的申请,耽误诉讼期限有不能抗拒的原因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事实,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事实等程序性问题,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本案中,被害人发现失窃后,立即报案,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发现桂花园小区别墅109号盗窃案中一部被盗的IPHONE5S手机由被告人王某使用,公安机关将王某抓获后,在王某随身携带的物品中以及其女友的暂住处、王某的销赃处查获了公诉机关指控王某实施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盗窃事实中的部分被窃物品,在第二节和第四节的作案现场中留有王某的DNA痕迹。本案中没有直接证据证实王某实施了盗窃,公诉机关根据上述间接证据推定王某实施了盗窃,即如果王某未实施盗窃为何会有失窃物品在王某及其女友处被查获,如果王某未实施盗窃为何会在失窃物品现场留有王某的DNA痕迹,故推定王某实施了盗窃。王某对此提出了反驳,辩称查获的物品系从他人处收购得来,其到过晨兴商务楼,但是去晨兴商务楼内的“香港纯K”找一女性朋友,因为喝醉酒了,不记得是否去过晨兴商务楼内的易成公司。该情况属于上述的第二种情形,即存在一个可反驳的推定时,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英国刑事法学家J·W·赛西尔·特纳将被告人的这种证明责任称为“必要的肯定性反证”。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当事人的利益,需要对罪行加以“否定性证明”,而用以进行这种否定证明的事实(如果存在的话)又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这时候,困难就产生了。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一旦控诉人提出的证据在一个有理智的人看来已足以对罪行作出肯定性的判定,那么,提出肯定性反证对罪行作出否定性证明的责任就落到了被告人身上。但是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无法提供被窃物品出售者以及所要寻找的“香港纯K”内的女性朋友的具体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情况,即无法提供足以反驳指控的证明。因此,在王某不能提出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为他不具有这种证据,相应地,就可以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是能够成立的。
二、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与适用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证据确实、充分’具有较强的的客观性,但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是否达到,还是要通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以达到主客观相统一。只有对案件已经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形成内心确信,才能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2]我国传统证据理论一般从逻辑学的角度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解释为“唯一性”“排他性”,而“排除合理怀疑”的实质也是要求事实裁判者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存在且为被告人所实施,对案件事实的存在达到了没有合理怀疑的程度,即表明依据案件证据材料得不出其他结论,因此可以形成确信。而对“合理怀疑”首先应当是在对全案证据进行慎重、细致分析推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有具体的证据事实为依据,具有实质性,同时还必须是符合经验与逻辑、具有合理性的怀疑,而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其次,“合理怀疑”应当具有足以能够动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效力。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时出现矛盾与疑点属于正常现象,不一定影响定案,只有那些能够动摇基本事实认定的怀疑才是定罪证明标准所指的“合理怀疑”。但有时并非只排除重大、实质的怀疑即可,故还需要根据具体案件进行把握。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概况为在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之后,事实裁判者对被告人犯罪的事实不再存在任何有证据支持的、符合经验与逻辑法则的疑问,产生了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内心确信。[3]
综合本案的全案证据,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盗窃的四节事实中,有的在王某及其女友处、王某销赃处查获了失窃的物品,有的在现场留有王某的DNA痕迹,王某对其辩称的系从他人处收购物品,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在晨兴商务楼内虽有“香港纯K”,但无法从“香港纯K”直接进入易成公司,进入易成公司需要密码或者门禁卡,外人不能随意出入,王某对于为何在易成公司和他人住宅内留有他的DNA痕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结合王某无业,并有赌博、吸毒等恶习,没有能力购买昂贵的钻石戒指、项链等物品以及他以前有多次因盗窃被处以行政处罚和判处刑罚的情况,虽然本案没有直接证据,但在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运用证据进行的关于王某实施盗窃的推定符合逻辑和经验,而王某对此推定提出的反驳无法证明;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王某实施盗窃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关于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规定,应当认定王某构成盗窃罪。
[1] 游伟、肖晚祥:《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5期。
[2]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3] 卞建林、张璐:《“排除合理怀疑”之理解与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现代刑事诉讼中,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已成为一项普遍性原则,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在特定情况下,被告人需承担证明责任。“排除合理怀疑”是我国“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在主观方面的解释与要求,是法官在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之后,产生的对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内心确信。
【案情】
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王某。
被告人王某,无业,因犯盗窃罪200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2011年6月2日刑满释放;因盗窃行为分别于2005年8月被处罚款100元,2005年9月被处行政警告,2005年10月被处治安拘留十四日、劳动教养一年,2007年8月被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因吸毒行为于2014年1月被责令接受社区戒毒三年。
2014年8月23日至12月23日期间,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多次入户或者进入他人公司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合计430余万元。具体如下:
1.2014年8月23日,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青湖路1070弄桂花园小区109号唐某父母家中,窃得一部价值3230元的苹果牌IPHONE5S手机、一台价值2032元的苹果牌IPAD平板电脑、一部三星手机以及现金若干。
2.2014年8月26日,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青湖路1023号晨兴商务楼206室上海易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公司)内,窃得一根男士铂金项链、香烟以及现金若干。
3.2014年12月19日,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1555弄佳邸别墅小区168号周某家中,窃得一部价值792元的苹果牌IPHONE4手机、一条价值11500元的千足金项链、一块欧米茄牌手表、一部苹果牌IPHONE5手机以及现金若干。
4.2014年12月17日至12月23日间,被告人王某窜至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1555弄佳邸别墅小区170号蒋某家中,窃得一枚钻石戒指(其中裸钻价值2749100元)、一个价值356600元的镶嵌钻石挂坠、一对价值49400元的TIFFANY牌钻石耳环、一条价值14800元的宝格丽牌红绿宝石加珍珠钻石项链、一条价值32000元的宝格丽牌18K项链、一个价值650000元的翡翠玉壶摆件、一个价值450000元的翡翠黄瓜形雕刻玉摆件、一条Pt750项链、一块TIFFANY牌白金钻石手表、一个和田玉龙鱼形雕刻摆件。
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月6日间,被告人王某独自或者指使其女友周某在贵州省遵义市将窃得的千足金项链、TIFFANY牌钻石耳环、宝格丽牌18K项链等赃物进行销赃。2015年1月8日,公安机关在贵州省遵义市将王某抓获。后公安机关在王某随身物品中,其女友周某居住的贵州省遵义市白沙路自来水家属院2栋201室内以及收购金银饰品的店主处分别查获被窃的苹果牌IPHONE5S手机、苹果牌IPAD平板电脑、苹果牌IPHONE4手机、千足金项链、裸钻、钻石挂坠、TIFFANY牌钻石耳环、宝格丽牌红绿宝石加珍珠钻石项链、宝格丽牌18K项链、翡翠玉壶摆件、翡翠黄瓜形雕刻玉摆件等财物,并将查获的上述物品发还给各名失主。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王某犯盗窃罪。被告人王某否认公诉机关指控的4节盗窃事实,辩称其未到过被害人唐某父母、周某以及蒋某家中,去过晨兴商务楼内的“香港纯K”找一个女性朋友,不记得是否经过易成公司,未实施盗窃,涉案物品系其从他人处收购的。其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王某犯有盗窃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恳请法院本着“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罚当其罪”的原则,对王某无正当理由、持有赃物的行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量刑。
【审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入户或者进入他人公司窃取他人财物,价值43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王某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王某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盗窃罪判处王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五十万元;查获的赃物予以追缴发还各名被害人(已发还),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某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被告人王某系零口供,其到案后始终否认实施过盗窃,辩称未到过现场,被查获的物品系从他人处收购得来。公诉机关一共起诉指控王某实施了四起盗窃,其中指控王某实施的第一节桂花园小区109号和第三节佳邸别墅小区168号盗窃案的主要证据有:被害人发现家中失窃后随即报案;公安人员抓获王某后,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了唐某父母失窃的苹果牌IPHONE5S手机和苹果牌IPAD平板电脑,从王某的女友周某暂住处查获了周某失窃的IPHONE4手机;王某将周某失窃的千足金项链出售给“恒生饰品”店的潘某,后公安机关从潘建处调取了该条千足金项链。公诉机关指控王某实施的第二节易成公司盗窃案的主要证据有:易成公司员工发现公司内发生盗窃案随即报案;从王某血样中提取的DNA,在D8S1179、D21S11等基因座上,与易成公司内所留果皮中具有相同的基因型,似然比率(LR)为2.27×1016,不能排除为王某所留;公诉机关指控王某实施的第四节佳邸别墅小区170号盗窃案的主要证据有:被害人发现家中失窃后随即报案,从被告人王某血样中提取的DNA,在D8S1179、D21S11等基因座上,与被害人蒋某家中卧室梳妆台抽屉上、玻璃上、大、小木盒上可疑斑迹处粘取物具有相同的基因型,似然比率(LR)为2.27×1016,不能排除为王某所留;从周某群暂住处查获了蒋某失窃的部分物品。
由于本案中没有关于王某实施盗窃的直接证据,而王某又对此提出辩解,根据现有证据能否认定王某实施盗窃,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在审判过程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对于起诉指控的第一节桂花园小区109号和第三节佳邸别墅小区168号失窃案,虽然王某及其女友周某持有部分失窃物品,但是没有证据证实王某曾到过犯罪现场,并通过实施盗窃行为获取失窃物品,故此两节不能认定王某构成盗窃罪,只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王某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起诉指控的第二节易成公司失窃案,虽然根据现场遗留物品的DNA鉴定结果,王某确曾到达过犯罪现场,但失窃物品均未在王某及其女友处起获,不能排除王某是正常进入该场所,仅凭王某到过现场,不足以认定其实施了盗窃行为。对于起诉指控的第四节佳邸别墅小区170号失窃案,虽然根据现场遗留物品的DNA鉴定结果,王某曾到达过犯罪现场,部分失窃物品在周某处起获,但是不能完全排除系他人盗窃,王某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赃物,以及王某以盗窃为目的到达现场,但因其他窃贼捷足先登而构成未遂的情形,故此节亦不能认定王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只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辩称从其随时携带的物品中和其女友周某暂住处查获的物品系从他人处收购得来,其应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但是王某无法提供出售者的具体情况;进入易成公司需要密码或者门禁卡,外人不能随意出入;晨兴商务楼内虽然有“香港纯K”,但是没法从“香港纯K”直接进入易成公司。王某亦称其到过晨兴商务楼,去“香港纯K”找一女性朋友,但是无法提供该女性朋友的具体情况。结合王某无业,并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应当认定其实施了盗窃。
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解决本案争议焦点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被告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以及如何理解与适用“排除合理怀疑”。
一、在例外情况下,被告人仍要对特定事项承担证明责任
现代刑事诉讼中,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已成为一项普遍性原则,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然而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尽管法文化和法传统有所不同,但在遵循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出于各种考虑,在立法和判例上都认为被告人在例外情况下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例如,根据英国1957年《谋杀法》的规定,控方指控被告人实施杀人行为,并举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有直接关系时,被告人如果否认谋杀,辩称意外事件所致或征得对方同意,则必须承担提出如此主张的证明责任。在美国证据法上,对于下列情形,被告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特定事项的义务:(1)如果被告方在辩护时提出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或不适于接受审判,被告方应对此提出证据加以证明;(2)如果某制定法规定,在没有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特殊情况或例外情况下,实施某种行为就是非法,那么被告方就有责任举证说明存在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特殊情况或例外情况;(3)如果被告人主张其行为曾取得许可、出于意外事件、受到胁迫、为了自卫等,此时便负有举证证明存在上述情况的责任;(4)如果被告方意图推翻制定法对某些事实的推定,或者意图援引法律条文中的但书、例外或豁免,这时被告方也负有证明责任。再如根据日本《刑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二人以上施加暴力致使他人受到伤害,在不能辨认所加害的轻重或不能辨认是何人所伤时,虽非共犯也应依共犯的规定处断。也就是说对同一人施暴的行为人,在检察官不能查明是谁造成何种伤害后果的情况下,嫌疑人负证明自己行为及其后果的责任。
借鉴国外关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立法和实践,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仅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而且在其他案件中和对某些程序性问题也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具体包括:一是被告人对某些积极抗辩事由应当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针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了新的主张,这一主张提出与否直接影响到罪与非罪或罪行轻重的认定,然而这一事实却并未被控方所掌握,被告人需对此承担证明责任。例如,控方指控甲犯有故意杀人罪,甲认可了故意杀人的事实,但提出了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这种情况下,甲对其辩护主张就需承担证明责任。因为如果甲不能举证证明其正当防卫的辩护主张具有合理的可能性,那么法官很可能要根据控方所指控的事实判甲有罪。二是存在一个可反驳的推定时,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对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构成要素以外而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从而影响到定罪量刑)的某些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方并不需要举证证明,或者仅需间接证据证明,即可推定这些要素存在时,如果被告人不对此提出证据进行辩解,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这里,被告人的辩解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义务。被告人这种提出证据进行辩解的义务是一种证明的负担,即证明责任。[1]三是对于独知的事实,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依据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实而提出某种主张的当事人必须证明他所依据的事实,否则将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四是主张精神不正常的事实,被告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对人们的行为一般都推定为是在神志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行为人是理解其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的,因而对行为人的精神状态是没有必要加以证明的。基于这一推定,控诉方在指控某人犯有某罪时,对被告人犯罪时精神状态的正常性是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的。一旦被告方提出行为时精神错乱,实际上是对这一推定的否定,因而证明责任就必然落在被告人的肩上。五是被告人主张其不在犯罪现场的,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犯罪时被告人是否在现场,是涉及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的重要事实之一。被告人声称自己在案件发生的时候不在犯罪现场,被告人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只要举出证据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就可以了,至于证据是否充分,并不影响其证明责任的完成。六是被告人主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七是对某些程序性问题,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广义上的证明对象说,程序法上的事实也可以作为证明对象。因此,关于回避的申请,耽误诉讼期限有不能抗拒的原因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事实,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事实等程序性问题,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本案中,被害人发现失窃后,立即报案,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发现桂花园小区别墅109号盗窃案中一部被盗的IPHONE5S手机由被告人王某使用,公安机关将王某抓获后,在王某随身携带的物品中以及其女友的暂住处、王某的销赃处查获了公诉机关指控王某实施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盗窃事实中的部分被窃物品,在第二节和第四节的作案现场中留有王某的DNA痕迹。本案中没有直接证据证实王某实施了盗窃,公诉机关根据上述间接证据推定王某实施了盗窃,即如果王某未实施盗窃为何会有失窃物品在王某及其女友处被查获,如果王某未实施盗窃为何会在失窃物品现场留有王某的DNA痕迹,故推定王某实施了盗窃。王某对此提出了反驳,辩称查获的物品系从他人处收购得来,其到过晨兴商务楼,但是去晨兴商务楼内的“香港纯K”找一女性朋友,因为喝醉酒了,不记得是否去过晨兴商务楼内的易成公司。该情况属于上述的第二种情形,即存在一个可反驳的推定时,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英国刑事法学家J·W·赛西尔·特纳将被告人的这种证明责任称为“必要的肯定性反证”。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当事人的利益,需要对罪行加以“否定性证明”,而用以进行这种否定证明的事实(如果存在的话)又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这时候,困难就产生了。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一旦控诉人提出的证据在一个有理智的人看来已足以对罪行作出肯定性的判定,那么,提出肯定性反证对罪行作出否定性证明的责任就落到了被告人身上。但是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无法提供被窃物品出售者以及所要寻找的“香港纯K”内的女性朋友的具体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情况,即无法提供足以反驳指控的证明。因此,在王某不能提出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为他不具有这种证据,相应地,就可以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是能够成立的。
二、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与适用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证据确实、充分’具有较强的的客观性,但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是否达到,还是要通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以达到主客观相统一。只有对案件已经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形成内心确信,才能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2]我国传统证据理论一般从逻辑学的角度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解释为“唯一性”“排他性”,而“排除合理怀疑”的实质也是要求事实裁判者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存在且为被告人所实施,对案件事实的存在达到了没有合理怀疑的程度,即表明依据案件证据材料得不出其他结论,因此可以形成确信。而对“合理怀疑”首先应当是在对全案证据进行慎重、细致分析推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有具体的证据事实为依据,具有实质性,同时还必须是符合经验与逻辑、具有合理性的怀疑,而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其次,“合理怀疑”应当具有足以能够动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效力。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时出现矛盾与疑点属于正常现象,不一定影响定案,只有那些能够动摇基本事实认定的怀疑才是定罪证明标准所指的“合理怀疑”。但有时并非只排除重大、实质的怀疑即可,故还需要根据具体案件进行把握。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概况为在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之后,事实裁判者对被告人犯罪的事实不再存在任何有证据支持的、符合经验与逻辑法则的疑问,产生了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内心确信。[3]
综合本案的全案证据,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盗窃的四节事实中,有的在王某及其女友处、王某销赃处查获了失窃的物品,有的在现场留有王某的DNA痕迹,王某对其辩称的系从他人处收购物品,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在晨兴商务楼内虽有“香港纯K”,但无法从“香港纯K”直接进入易成公司,进入易成公司需要密码或者门禁卡,外人不能随意出入,王某对于为何在易成公司和他人住宅内留有他的DNA痕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结合王某无业,并有赌博、吸毒等恶习,没有能力购买昂贵的钻石戒指、项链等物品以及他以前有多次因盗窃被处以行政处罚和判处刑罚的情况,虽然本案没有直接证据,但在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运用证据进行的关于王某实施盗窃的推定符合逻辑和经验,而王某对此推定提出的反驳无法证明;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王某实施盗窃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关于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规定,应当认定王某构成盗窃罪。
[1] 游伟、肖晚祥:《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5期。
[2]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3] 卞建林、张璐:《“排除合理怀疑”之理解与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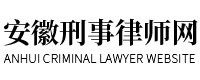
安徽刑事律师网
向您推荐
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与“排除合理怀疑”的把握
长按屏幕
保存至相册分享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