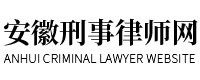什么是不真正的持有型犯罪?
2022/5/18
在对“非法持有”的判断上,不真正的持有型犯罪并不像真正的持有型犯罪那样一目了然,因此在罪状的描述上,不可能像真正的持有型犯罪那样简单地以“非法持有”一笔带过。
在不真正的持有型犯罪中,“非法持有”相对于真正的持有型犯罪,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质性的判断。举例说明,作为持有型犯罪,我国刑法典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持有对象——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与真正的持有型犯罪有本质的不同,它并不是“违法行为的产物”,也不是“我国严格管控的物品”,因此对其的“非法持有”不能像真正的持有型犯罪那样做简单的叙明,而必须进行实质的解释。从该罪的罪状描述“……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就能看出,行为人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和“不能说明来源”的情节是“非法所得”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是符合持有型犯罪入罪门槛的“非法持有”,才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
由于不真正的持有型犯罪的特点,使得我们不能像真正的持有型犯罪那样很容易区分非法持有和合法持有,但是也正是这种对“非法持有”的实质解释,使得在不真正的持有型犯罪中束手无策的“依附于一般违法行为”的持有能够被排除出犯罪圈,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不能说明来源”的限定。学界中,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不能说明来源”的性质认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能说明来源”的限定条件只是“程序上的限定”,即司法人员责令其说明来源而行为人不能说明来源,类似自诉案件中的行为人的举报。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说明来源”的限定则是构成要件中的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或者说将“能够说明来源”理解为该罪的正当化事由。在笔者看来,既然“不能说明来源”是对非法持有的实质解释,那么它就不可能只有程序意义,而作为一种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它能够尽可能地将依附于合法行为的持有和依附于一般违法行为的持有排除出犯罪圈。
首先,“不能说明来源”是建立在无法查明财产的真实来源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上文所述,持有型犯罪的成立是建立在“不能确定”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能够确定财产的来源,就应当以其来源认定其性质——具体的犯罪、无罪或者是违规违纪。
其次,在无法查明的基础之上将行为人的“不能说明来源”的情形认定为犯罪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一般人的共识之上:其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持有的财产的来源;其二,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关于第一点共识并不存在疑问,而第二点共识则能够概括如下:如果行为人持有了“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如上文所述,其持有可能依附于三种行为,第一种是合法行为,即合法持有,例如合法获得的赠与或者遗产;第二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虽然是非法持有,但是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例如行为人挪用公款后对公款的持有,但是其挪用的行为还没有达到挪用公款罪的成立条件;第三种情况是犯罪行为,例如受贿或者贪污后对赃款的持有。在前两种情况下,为了防止更为严重的后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般人都会如实说明自己的财产来源以换取相对来说较轻的后果。
因此,如果出现了行为人不能说明,拒不说明或者是不如实说明的情况时,根据一般人的共识,应当可以推断其持有所依附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当然,前提是无法查证其持有所依附的具体的犯罪到底是什么,否则就应当以其所依附的犯罪定罪处罚——如此一来,相对于真正的持有型犯罪,作为对“非法持有”做实质解释的不真正的持有型犯罪,就给将依附于一般违法行为的持有排除出犯罪圈留下了余地。
来源:互联网